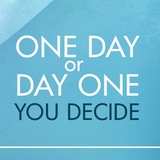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观点 大多数交易都有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但免费让我们忘记了不利的那面。免费使我们造成一种情绪冲动,我们误认为免费物品大大高于它的真正价值。为什么?我认为是由于人类本能的惧怕损失。免费的真正诱惑力与这种惧怕心理密切相关。我们选择免费物品不会有风险,如果我们选择的物品不是免费的,那就有蒙受损失的风险。
#laugh @斜月三星: 结绳记事多好。抚摸着草绳上的一个个绳节,有的代表爱情,有的代表曾捉到一只野猪。//@阿圳:吃着肉喝着汤,看着龟甲上的诗歌,是其他文字载体都望尘莫及的 //@刘世伟: 竹简相碰清脆的声音,是任何纸质书籍无法比拟的。//@彭彭:一本沁着墨香的书捧在手心,展在眼前的感觉,是任何电子书不可能比拟的味道~
### 第二语言学习,到底有没有“窗口期”?
大量的案例和统计数据分析后发现,竟然是一笔糊涂账。大致的结论是,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关键期”并没有那么关键。关于“学外语不能错过‘窗口期’”这样的建议,从严谨的科研角度来看,是无法得出的。
“窗口期”这个说法在语言学习上很形象,让人觉得仿佛有一个时间“窗口”,一旦时间一过,这个“窗口”就关上了,孩子的外语就再也学不会了。早些年,不少父母受“起跑线”理论的影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尽量让孩子尽早开始学外语。现在见识广了,听得多了,对“起跑线”的焦虑有所缓解,但“窗口期”这个概念依然让人揪心。大家担心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就会耽误孩子一生的外语学习。
更准确一点来说,这个“窗口期”应该叫作“关键期”(Critical Period)。这一概念原本属于发展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引入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关键期假说”,试图解释人类习得语言的过程。该假说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一些与语言习得相关的生物机制,这些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到了青春期开始时会完全消失。因此,人类出生头几年是学会语言的重要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一关键期,就可能无法学会语言。
语言“关键期”假说提出后,得到了广泛关注和一定程度的认同。然而,它在学术界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证明。这个术语是类比哺乳动物视觉能力发展过程得出的。研究动物视觉发展时,可以在实验室里控制条件,例如在关键期内不让实验动物接触光源,从而得出错过关键期后视觉能力无法正常发展的实验结果。这种方式能够证明关键期的重要性。但在人类语言发展研究中,无法展开类似的实验。语言关键期的论证只能依靠推论,这难免引发学术争议。
部分能够得到的实证数据主要来自于对大脑受损个例和“狼孩”的研究。有些大脑受损的案例表明,语言能力受到影响。如果损伤发生在关键期之前,语言能力还有恢复的可能;但若损伤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就很难恢复了。然而,这类研究还需要考虑大脑受损的具体部位及是否涉及其他区域的创伤等问题,难以控制变量。“狼孩”的例子则表明,人类孩子若错过语言关键期,就无法有效学会语言,尤其是句法结构。然而,即便是“狼孩”的情况,也存在不同声音:有人认为,“狼孩”的智力发展也受到了破坏,因此无法区分究竟是错过了语言关键期,还是整个认知能力发展受限导致的语言障碍。
语言关键期假说很快被应用到第二语言领域。这次,实证数据相对容易获取。毕竟第二语言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年龄组的对比来观察关键期的影响。结果是,虽然有大量案例和统计数据,但得出的结论依然混乱。一个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些成年后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马克思在51岁开始学习俄语,最终达到了能在图书馆阅读原文的程度。这一现象与第一语言中的“狼孩”截然不同。因此,关键期假说在第二语言领域的适用性大打折扣,关键期的时间范围也被逐渐放宽,一般被界定为2到12岁之间。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更宽泛的术语,如“敏感期”“最佳期”等,以回避“关键期”这个不那么关键的说法。
看到“关键期”之后仍能学好外语的情况后,有研究进一步细化,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语言内容入手分析。在语音层面,问题较为清晰:年龄越小,语音学习的优势越明显;而青春期之后,要完全形成纯正口音的概率就很低。因此,关键期对第二语言语音的影响基本达成了共识。
语法方面,研究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也就是说,孩子从低龄开始学习,在句法结构上并未表现出明显优于成人的优势。这一点与第一语言形成鲜明对比。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人类通过漫长的进化,在大脑中形成了一种“通用语法”(UG)机制,因此无论孩子出生在哪里,都能学会当地语言作为母语,且句法结构是无需教导的,自然形成的。这一过程的时间窗口大约在四岁以前。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中,语法需要专门教导,并且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终生都难以达到完美,没有明显的关键期。
词汇方面,成年人的学习优势反而更为突出。成年人积累词汇的速度比孩子快得多。词汇问题本身则更加复杂,因为在母语中,语音和语法系统会早早形成并固定,但词汇量的增长可以持续到中年,大约在35到40岁达到顶峰。此外,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词汇并不完全由大脑语言中枢控制,而是分布在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因此,成年人词汇学习更快的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关键期”在第二语言中的意义,因为词汇积累才是外语学习中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环节。
关于青春期后大脑的变化,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青春期前,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尚未完成,语言处理尚未完全集中到语言中枢,因此大脑的可塑性较高。另一个假说认为,大脑前额皮质在青春期前尚未发育完全,而这一发育一旦完成,人类幼年期的一些自然本能就会被压制,再也无法体现。但无论如何,人类的大脑和语言机制仍是未解之谜,目前的科研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研究现象是,青春期前习得的语言可能会被完全遗忘。儿童在脱离语言环境后,甚至会忘记母语。研究表明,青春期前学的语言若不使用,可能会被彻底遗忘。这一结论为“大脑在青春期前后发生关键变化”的假设提供了进一步证明,也提示我们:太早学习外语可能会因遗忘而浪费时间。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即使考虑教学应用层面,也可以观察到,虽然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但青春期后开始学习的人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从科研角度看,无法得出“外语学习必须赶在关键期之前,否则就学不成”的结论。对外语学习的年龄与效果保持适度敏感即可,不必过于纠结于“关键期”或“敏感期”这些传说中的时间窗口。
#网摘
大量的案例和统计数据分析后发现,竟然是一笔糊涂账。大致的结论是,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关键期”并没有那么关键。关于“学外语不能错过‘窗口期’”这样的建议,从严谨的科研角度来看,是无法得出的。
“窗口期”这个说法在语言学习上很形象,让人觉得仿佛有一个时间“窗口”,一旦时间一过,这个“窗口”就关上了,孩子的外语就再也学不会了。早些年,不少父母受“起跑线”理论的影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尽量让孩子尽早开始学外语。现在见识广了,听得多了,对“起跑线”的焦虑有所缓解,但“窗口期”这个概念依然让人揪心。大家担心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就会耽误孩子一生的外语学习。
更准确一点来说,这个“窗口期”应该叫作“关键期”(Critical Period)。这一概念原本属于发展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引入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关键期假说”,试图解释人类习得语言的过程。该假说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一些与语言习得相关的生物机制,这些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到了青春期开始时会完全消失。因此,人类出生头几年是学会语言的重要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一关键期,就可能无法学会语言。
语言“关键期”假说提出后,得到了广泛关注和一定程度的认同。然而,它在学术界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证明。这个术语是类比哺乳动物视觉能力发展过程得出的。研究动物视觉发展时,可以在实验室里控制条件,例如在关键期内不让实验动物接触光源,从而得出错过关键期后视觉能力无法正常发展的实验结果。这种方式能够证明关键期的重要性。但在人类语言发展研究中,无法展开类似的实验。语言关键期的论证只能依靠推论,这难免引发学术争议。
部分能够得到的实证数据主要来自于对大脑受损个例和“狼孩”的研究。有些大脑受损的案例表明,语言能力受到影响。如果损伤发生在关键期之前,语言能力还有恢复的可能;但若损伤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就很难恢复了。然而,这类研究还需要考虑大脑受损的具体部位及是否涉及其他区域的创伤等问题,难以控制变量。“狼孩”的例子则表明,人类孩子若错过语言关键期,就无法有效学会语言,尤其是句法结构。然而,即便是“狼孩”的情况,也存在不同声音:有人认为,“狼孩”的智力发展也受到了破坏,因此无法区分究竟是错过了语言关键期,还是整个认知能力发展受限导致的语言障碍。
语言关键期假说很快被应用到第二语言领域。这次,实证数据相对容易获取。毕竟第二语言学习者可以通过不同年龄组的对比来观察关键期的影响。结果是,虽然有大量案例和统计数据,但得出的结论依然混乱。一个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些成年后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马克思在51岁开始学习俄语,最终达到了能在图书馆阅读原文的程度。这一现象与第一语言中的“狼孩”截然不同。因此,关键期假说在第二语言领域的适用性大打折扣,关键期的时间范围也被逐渐放宽,一般被界定为2到12岁之间。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更宽泛的术语,如“敏感期”“最佳期”等,以回避“关键期”这个不那么关键的说法。
看到“关键期”之后仍能学好外语的情况后,有研究进一步细化,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语言内容入手分析。在语音层面,问题较为清晰:年龄越小,语音学习的优势越明显;而青春期之后,要完全形成纯正口音的概率就很低。因此,关键期对第二语言语音的影响基本达成了共识。
语法方面,研究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也就是说,孩子从低龄开始学习,在句法结构上并未表现出明显优于成人的优势。这一点与第一语言形成鲜明对比。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人类通过漫长的进化,在大脑中形成了一种“通用语法”(UG)机制,因此无论孩子出生在哪里,都能学会当地语言作为母语,且句法结构是无需教导的,自然形成的。这一过程的时间窗口大约在四岁以前。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中,语法需要专门教导,并且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终生都难以达到完美,没有明显的关键期。
词汇方面,成年人的学习优势反而更为突出。成年人积累词汇的速度比孩子快得多。词汇问题本身则更加复杂,因为在母语中,语音和语法系统会早早形成并固定,但词汇量的增长可以持续到中年,大约在35到40岁达到顶峰。此外,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词汇并不完全由大脑语言中枢控制,而是分布在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因此,成年人词汇学习更快的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关键期”在第二语言中的意义,因为词汇积累才是外语学习中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环节。
关于青春期后大脑的变化,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青春期前,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尚未完成,语言处理尚未完全集中到语言中枢,因此大脑的可塑性较高。另一个假说认为,大脑前额皮质在青春期前尚未发育完全,而这一发育一旦完成,人类幼年期的一些自然本能就会被压制,再也无法体现。但无论如何,人类的大脑和语言机制仍是未解之谜,目前的科研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研究现象是,青春期前习得的语言可能会被完全遗忘。儿童在脱离语言环境后,甚至会忘记母语。研究表明,青春期前学的语言若不使用,可能会被彻底遗忘。这一结论为“大脑在青春期前后发生关键变化”的假设提供了进一步证明,也提示我们:太早学习外语可能会因遗忘而浪费时间。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即使考虑教学应用层面,也可以观察到,虽然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但青春期后开始学习的人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从科研角度看,无法得出“外语学习必须赶在关键期之前,否则就学不成”的结论。对外语学习的年龄与效果保持适度敏感即可,不必过于纠结于“关键期”或“敏感期”这些传说中的时间窗口。
#网摘
转贴:很多伟大的程序员都是在他们大学的第二年就开始编程了。当他们离开学校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了。还有,有些很神奇的程序员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编程的艺术了。我也认识好几个人在他们十几岁或更小时就写出来一些不算小的程序了。这些信息你是在简历上找不到的,需要你在面试中把它们引诱出来。 http://www.aqee.net/finding-awesome-developers-in-programming-interviews/
#网友语录 转@oliveios 允许一切发生,积极面对。转@李没 1.接受普通人的人生没有意义
2.接受在爱情里,对方先离开3.接受婚姻随时崩塌 4.接受一切变故 5.接受无聊,与它共处
2.接受在爱情里,对方先离开3.接受婚姻随时崩塌 4.接受一切变故 5.接受无聊,与它共处
不害怕别人说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不好,是成为一个好匠人的第一步。
@5306 今天早晨突然想起今年去世的大伯(WEI LIDONG)。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大伯的离世,也是他那座图书馆的湮灭。而在那里也有我的小小部分随之湮灭。
我的大伯不仅仅是我的大伯。在我6岁到8岁那两年,我是他的养子。我现在用的名字,也是大伯在那时候改的。1958年黑旺铁矿招工,他去了,从此成了工人阶级。但是他不能带家属,因此只能利用每年一个月探亲假回老家探亲,几十年如此。大伯没有子女,我唯一的姐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大伯。在我五岁那年有了妹妹,父亲大概觉得他还可以再有一个儿子,就在我六岁那年把我也过继给了大伯。因此平日里家里平时只有爷爷,大妈,姐姐,和我。在我的家乡,管爸妈叫爹和娘。不知道是不是规矩,他们让我管大妈叫亲娘。以至于后来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之后,甚至到了今天,见到大妈我还是会管她叫亲娘。怪异的是,自我记事起,我就一直管大伯叫大爸爸,不记得有人让我改这个称呼。
然而由于两家只隔了几百米,我仍然能很经常地溜回我亲生父母的家。到我8岁那年,因为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什么由头,我再也不想住到大伯家里,就跑到大队里找书记坚决要求把我的户口改回来。细节我已经不知道,但我就此又回到了亲生父母家里。
然而那两年里还是有很多记忆不能忘。有一年大伯带我去了矿上,于是我知道大伯的工作是开电铲,把爆破下来的铁矿石铲起来装到用来拉矿石的专门的小火车上。
我记得在那儿交了好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后来还成了我的同学(GuoGang)。我记得晚上去水渠边的大礼堂看电影。我记得和小伙伴们自己咬面筋沾知了。(所以那一定是个夏天了!)我记得等那个绿皮火车开过来就该回家吃饭了。我隐约记得山里有一个绿莹莹的池塘,里面有红色的金鱼。
我还记得大伯把我留在一个小屋里躲避开矿的爆破。一声巨响之后碎石块打到门上当当的响。
我记得矿上有一次出了人命事故,一个工友拿铁钎去够树上的香椿,但不幸搭到了高压线上。
我记得有一回大伯带我去看民兵打枪,那枪沉得我都提不起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摸真枪呢!
在矿上我第一次吃到粗面包,虽然挺硬,可是是甜的呢!
这些记忆,本就微不足道,等我将来死去,也就再无人知晓。我今天写下这些,一是怀念逝去的大伯,也是感谢他让我见识了外面的世界。
我的大伯不仅仅是我的大伯。在我6岁到8岁那两年,我是他的养子。我现在用的名字,也是大伯在那时候改的。1958年黑旺铁矿招工,他去了,从此成了工人阶级。但是他不能带家属,因此只能利用每年一个月探亲假回老家探亲,几十年如此。大伯没有子女,我唯一的姐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大伯。在我五岁那年有了妹妹,父亲大概觉得他还可以再有一个儿子,就在我六岁那年把我也过继给了大伯。因此平日里家里平时只有爷爷,大妈,姐姐,和我。在我的家乡,管爸妈叫爹和娘。不知道是不是规矩,他们让我管大妈叫亲娘。以至于后来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之后,甚至到了今天,见到大妈我还是会管她叫亲娘。怪异的是,自我记事起,我就一直管大伯叫大爸爸,不记得有人让我改这个称呼。
然而由于两家只隔了几百米,我仍然能很经常地溜回我亲生父母的家。到我8岁那年,因为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什么由头,我再也不想住到大伯家里,就跑到大队里找书记坚决要求把我的户口改回来。细节我已经不知道,但我就此又回到了亲生父母家里。
然而那两年里还是有很多记忆不能忘。有一年大伯带我去了矿上,于是我知道大伯的工作是开电铲,把爆破下来的铁矿石铲起来装到用来拉矿石的专门的小火车上。
我记得在那儿交了好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后来还成了我的同学(GuoGang)。我记得晚上去水渠边的大礼堂看电影。我记得和小伙伴们自己咬面筋沾知了。(所以那一定是个夏天了!)我记得等那个绿皮火车开过来就该回家吃饭了。我隐约记得山里有一个绿莹莹的池塘,里面有红色的金鱼。
我还记得大伯把我留在一个小屋里躲避开矿的爆破。一声巨响之后碎石块打到门上当当的响。
我记得矿上有一次出了人命事故,一个工友拿铁钎去够树上的香椿,但不幸搭到了高压线上。
我记得有一回大伯带我去看民兵打枪,那枪沉得我都提不起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摸真枪呢!
在矿上我第一次吃到粗面包,虽然挺硬,可是是甜的呢!
这些记忆,本就微不足道,等我将来死去,也就再无人知晓。我今天写下这些,一是怀念逝去的大伯,也是感谢他让我见识了外面的世界。
#网友语录 是你的SSR 人到中年更懂得能做到我妈那样是很难得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工作赚钱,孩子小时在家她就顾好孩子吃睡,孩子长大了她放手都没有缓冲期的,也几乎不要求孩子,说她是尊重我吧,也不是,更像是尊重她自己和那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边界感。听自己想听的看自己想看的,纯开朗。
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大乡村,一草一木都很亲切呢!
现代汉语是经过简化的,用词高度简化,很多字被舍弃了。
不要忘记文言文中脍炙代表烤肉和切肉,樗是一种蚕,隰是低湿的地方。騑(fei):三岁的马。駣(tao):三四岁的马。騱(xi):前脚全白的马。騚 (qian):四蹄全白的马。驓(ceng):膝下白色的马。驠(yan):屁股毛色白的马。
这些玩意全不用了。#网摘
不要忘记文言文中脍炙代表烤肉和切肉,樗是一种蚕,隰是低湿的地方。騑(fei):三岁的马。駣(tao):三四岁的马。騱(xi):前脚全白的马。騚 (qian):四蹄全白的马。驓(ceng):膝下白色的马。驠(yan):屁股毛色白的马。
这些玩意全不用了。#网摘
#书摘 乔小刀:如果你不是完美主义者,就能轻松的实现快乐。因为只要是和我周围相关发生的事情,我和路子基本上都用小照相机拍下来,而且是互相拍,统一保存。当我今天要写书炫耀我的成就时,拿出当年的照片就能充分的证明这事是真的。最后悟到摄影其实就是记录片段的时光,真正感动你的是拍下当时的自然影像。如果你不是职业摄影师,那就胡乱拍吧,无论多丑也不要删掉。过上十年,再丑的照片都是美的。
你的问题很好, 你的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