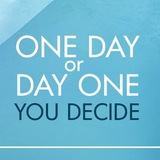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代议制政府》的作者密尔,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这是密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书摘
#书摘 The loss of the spark isn't actually about the loss of the spark. It's about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书摘 城南旧事
“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 ,灯光照在白雪上 ,又平又亮 。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 ,一层层铺上去 。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 ,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 《下雪 》的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 ,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 ,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 。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让我不禁想起下面这首诗: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 ,灯光照在白雪上 ,又平又亮 。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 ,一层层铺上去 。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 ,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 《下雪 》的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 ,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 ,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 。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让我不禁想起下面这首诗: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心理学家研究过这种现象——收藏这一行为在人痛苦时能够带来的甜蜜慰藉。心理学家维尔纳·明斯特伯格在数十年中采访了多位有收藏癖的人,并在《收藏:难以控制的激情》(Collecting: An Unruly Passion)一书中写道,在一个人经历某种“分离、失去或伤痛”后,其收藏欲通常会变得格外狂热。每获得一件新的藏品,收藏者就陷入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之中。格拉纳达大学的弗朗西斯卡·洛佩斯-托雷西利亚斯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收藏者,她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人们在沮丧或焦虑时,会通过收藏行为来缓解伤痛。“当人们心中感到无助时,”她写道,“强迫性的收藏行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而唯一的危险,明斯特伯格警示道,就是似乎存在一条界线,任何强迫症都是如此。一旦越过该界线,收藏就会从“令人喜悦”转变为“让人倾家荡产”。#书摘 《鱼 不存在》
#书摘 Being able to reason precisely and formally about syntax and semantics is a vital skill when working on a language. But, personally, I learn best by doing. It’s hard for me to wade through paragraphs full of abstract concepts and really absorb them. But if I’ve coded something, run it, and debugged it, then I get it.
"Crafting Interpreters"
"Crafting Interpreters"
他对电脑一窍不通,在他的印象里,计算机似乎很危险,甚至不吉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人对计算机都有这种反乌托邦的看法。对这些咯吱咯吱咀嚼数字的机器,人们还抱着怀疑的态度,有的时候还很反感,因为他们有控制人类的倾向。计算机似乎总是要人类来服从它们的意志,强迫人们除了服从电脑的命令外做不了什么。
这使计算机的名声很不好,也让人们对为计算机编程这样的工作没有好感。几乎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个程序员,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承认,那么人们会觉得他很奇怪。在卡特勒从奥利维特学院毕业前几年,最顶尖的程序员在荷兰,有一个物理学家在他的结婚证上注明自己是程序员。令他沮丧的是,官方人员以没有这样的工作拒绝了他的结婚申请。#书摘 《观止》
这使计算机的名声很不好,也让人们对为计算机编程这样的工作没有好感。几乎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个程序员,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承认,那么人们会觉得他很奇怪。在卡特勒从奥利维特学院毕业前几年,最顶尖的程序员在荷兰,有一个物理学家在他的结婚证上注明自己是程序员。令他沮丧的是,官方人员以没有这样的工作拒绝了他的结婚申请。#书摘 《观止》
#书摘 第二天早上,我走出蒙古包,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迷人的山谷。雾气已经消散,到处是鲜亮的绿色。云影投射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阳光下的卡拉科尔河跳跃着。马群像碎芝麻一样,散落在起伏的山水间。(读到这里,我非常非常怀念在高山营地里的清晨,还有那遍地的金莲花呀...
#书摘 埃利斯 REBT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人们并非被不利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而是被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观念搞得心烦意乱的,人们带着这些想法,或者产生健康的负性情绪,如悲哀、遗憾、迷惑和烦闷,或者产生不健康的负性情绪,如抑郁、暴怒、焦虑和自憎。
当人们按理性去思考、去行动时,他们就会是愉快的、行之有效的人。人的情绪伴随思维产生,情绪上的困扰是非理性的思维所造成。理性的信念会引起人们对事物适当、适度的情绪反应;而非理性的信念则会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当人们坚持某些非理性的信念,长期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之中时,最终将会导致情绪障碍的产生。
非理性信念的特征有如下几项。①绝对化的要求。比如“我必须获得成功”“别人必须很好地对待我”“生活应该是很容易的”,等等。②过分概括化。即以某一件事或某几件事的结果来评价整个人。过分概括化就好像以一本书的封面来判定一本书的好坏一样。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以他是否聪明,是否取得了成就等来评价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具有人性。他因此主张不要去评价整体的人,而应代之以评价人的行为、行动和表现,每一个人都应接受自己和他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人类一员(无条件的自我接纳和接纳别人)。③糟糕至极。这是一种认为如果一件不好的事发生将会非常可怕、非常糟糕乃至堪比灾难的想法。非常不好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发生,尽管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事情绝对不该发生。我们将努力去接受现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改变这种状况,在不可能时学会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下去。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简单来说,就是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并与之辩论,从而达到“无条件的自我接纳”的境界。
大部分心理治疗的流派会比较倾向于使用或认知,或行为,或情绪的方法,但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流派,它三种方法都使用,并清楚地认识到认知、行为、情绪是相互作用的。所以,我们以一种情绪和行为的模式使用认知技术,我们以一种认知和行为的模式使用情绪技术,我们以一种认知和情绪的模式使用行为技术。
当人们按理性去思考、去行动时,他们就会是愉快的、行之有效的人。人的情绪伴随思维产生,情绪上的困扰是非理性的思维所造成。理性的信念会引起人们对事物适当、适度的情绪反应;而非理性的信念则会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当人们坚持某些非理性的信念,长期处于不良的情绪状态之中时,最终将会导致情绪障碍的产生。
非理性信念的特征有如下几项。①绝对化的要求。比如“我必须获得成功”“别人必须很好地对待我”“生活应该是很容易的”,等等。②过分概括化。即以某一件事或某几件事的结果来评价整个人。过分概括化就好像以一本书的封面来判定一本书的好坏一样。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以他是否聪明,是否取得了成就等来评价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具有人性。他因此主张不要去评价整体的人,而应代之以评价人的行为、行动和表现,每一个人都应接受自己和他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人类一员(无条件的自我接纳和接纳别人)。③糟糕至极。这是一种认为如果一件不好的事发生将会非常可怕、非常糟糕乃至堪比灾难的想法。非常不好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发生,尽管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事情绝对不该发生。我们将努力去接受现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改变这种状况,在不可能时学会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下去。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简单来说,就是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并与之辩论,从而达到“无条件的自我接纳”的境界。
大部分心理治疗的流派会比较倾向于使用或认知,或行为,或情绪的方法,但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流派,它三种方法都使用,并清楚地认识到认知、行为、情绪是相互作用的。所以,我们以一种情绪和行为的模式使用认知技术,我们以一种认知和行为的模式使用情绪技术,我们以一种认知和情绪的模式使用行为技术。
“没有人能审判爱情,”她说:“每一件不快乐的爱情,总有一方说被另一方欺骗、玩弄。〞
...
“—个爱上别人的人,包括我自己,总以为别人应当以对等的爱情回报她,”她幽幽地说:“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多么明显的不公平。”
...
“在爱情上,女人要比男人诚实,比男人勇敢多了。” 然而他没有说出口来。
#书摘 陈映真 《夜行货车》
...
“—个爱上别人的人,包括我自己,总以为别人应当以对等的爱情回报她,”她幽幽地说:“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多么明显的不公平。”
...
“在爱情上,女人要比男人诚实,比男人勇敢多了。” 然而他没有说出口来。
#书摘 陈映真 《夜行货车》
从小到大,他惯常听见他以那快速的话锋抱怨校长,抱怨训导;抱怨将近三十年前招致他破产的金融波动;抱怨政治;抱怨天气;抱怨“外省人”•••
“从小到大,我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地长大。”他说。他的小而饱满的脸,因多量的酒而愈益苍白起来。“家庭的贫穷、父亲的失意,简直就是绳索,就是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让我觉得,以家境论,以父亲的失意,我原本早就没有求学的机会的,”他说:“而我得以一级一级地受教育,读完大学,又读完硕士。”他面有怒色,“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砰砰地捶着胸脯说。
“你喝多了。”她温柔地说。
“孩子,你看,我们牺牲自己,让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得出人头地,”他讥嘲地说:“我们牺牲了没关系,孩子,走哇!往那个地方走,那个我们这一辈子想到却无法抵达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他一会儿扬手,一会儿扬眉,表情十足地说着,于是便哼哼地笑了起来。
#书摘
“从小到大,我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地长大。”他说。他的小而饱满的脸,因多量的酒而愈益苍白起来。“家庭的贫穷、父亲的失意,简直就是绳索,就是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让我觉得,以家境论,以父亲的失意,我原本早就没有求学的机会的,”他说:“而我得以一级一级地受教育,读完大学,又读完硕士。”他面有怒色,“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砰砰地捶着胸脯说。
“你喝多了。”她温柔地说。
“孩子,你看,我们牺牲自己,让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得出人头地,”他讥嘲地说:“我们牺牲了没关系,孩子,走哇!往那个地方走,那个我们这一辈子想到却无法抵达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他一会儿扬手,一会儿扬眉,表情十足地说着,于是便哼哼地笑了起来。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