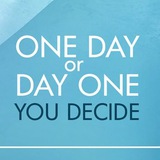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王海鹏Seal:不认为自己对,就不会认为别人错。不认为自己知道,就不会认为别人无知。不认为自己智商高,就不会认为别人是白痴。//@陈加兴:嘻嘻 很有道理//@诺铁: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网友语录
安子 “Criminal lawyers see bad people at their best. Divorce lawyers see good people at their worst.”
刑事律师看到最好的坏人,离婚律师看到最坏的好人。
#网友语录 (何为好人?何为坏人?这是一个问题)
刑事律师看到最好的坏人,离婚律师看到最坏的好人。
#网友语录 (何为好人?何为坏人?这是一个问题)
@25820 他说穆尔克里斯全家都是不想干任何活的人。他震惊地看到,虽是个出色的女裁缝,托米的母亲却衣衫褴褛地晃悠,托米自己虽是个合格的木匠,但他们屋子里的每一张椅子都有一条断腿。他在日记里径直说托米——“我在这儿完全依赖于他”——是“不可靠的”。
无论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邻居莫蒂默一家认为他完全疯了,不愿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禁止他走进他们的地界,理由是他会吓坏他们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罗斯洛后面的山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条长而迂回的路线。有一次他这样散步时,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当工具在路上的泥地里画一个轮廓图(一个兔-鸭图?),他站着,长时间全神贯注盯着这张图,然后又走了起来。这事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还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声打乱了维特根斯坦的专注,他猛烈爆发了。事实上,他留给莫蒂默家的印象,与他先前留给奥地利乡下村民的印象颇为雷同。
托米也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点怪。但部分因为对德鲁利家的忠诚(迈尔斯·德鲁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为开始喜欢“教授”的相伴,他愿意竭尽所能使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居住尽量舒适和愉快。例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满足维特根斯坦严格的清洁和卫生标准。按维特根斯坦的建议,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还送去自己用过的茶叶。每天早晨,茶叶洒在厨房地板上吸污垢,然后扫掉。维特根斯坦还叫托米弄掉屋子里的“甲壳动物”(土鳖虫)。托米的做法是,给整个屋子喷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毕生害怕每一种虫子的维特根斯坦对结果感到满意,他情愿面对窒息的威胁,也不愿意看见土鳖虫。
罗斯洛农舍有两个房间,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度过。但没用厨房做饭。在罗斯洛时,他几乎完全依靠从戈尔韦的一家杂货店里订购的罐头食品。托米挺担忧他的饮食。“罐头食品会吃死你”,他有一次说。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阴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维特根斯坦把厨房改作书房,托米早晨去时,常常发现他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往夹起来的散页上写着什么。几乎每天都有一堆丢掉的纸页,烧掉它们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罗斯洛时听见维特根斯坦的说话声,进屋后惊讶地发现只有“教授”自个。“我以为你有个伴在这儿呢,”他说。“我是有,”维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个很亲爱的朋友——我自己——谈话。”在他这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这句话得到了呼应:
几乎我的所有写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谈话。我跟自己促膝而谈的话。
#书摘
无论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邻居莫蒂默一家认为他完全疯了,不愿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禁止他走进他们的地界,理由是他会吓坏他们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罗斯洛后面的山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条长而迂回的路线。有一次他这样散步时,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当工具在路上的泥地里画一个轮廓图(一个兔-鸭图?),他站着,长时间全神贯注盯着这张图,然后又走了起来。这事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还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声打乱了维特根斯坦的专注,他猛烈爆发了。事实上,他留给莫蒂默家的印象,与他先前留给奥地利乡下村民的印象颇为雷同。
托米也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点怪。但部分因为对德鲁利家的忠诚(迈尔斯·德鲁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为开始喜欢“教授”的相伴,他愿意竭尽所能使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居住尽量舒适和愉快。例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满足维特根斯坦严格的清洁和卫生标准。按维特根斯坦的建议,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还送去自己用过的茶叶。每天早晨,茶叶洒在厨房地板上吸污垢,然后扫掉。维特根斯坦还叫托米弄掉屋子里的“甲壳动物”(土鳖虫)。托米的做法是,给整个屋子喷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毕生害怕每一种虫子的维特根斯坦对结果感到满意,他情愿面对窒息的威胁,也不愿意看见土鳖虫。
罗斯洛农舍有两个房间,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度过。但没用厨房做饭。在罗斯洛时,他几乎完全依靠从戈尔韦的一家杂货店里订购的罐头食品。托米挺担忧他的饮食。“罐头食品会吃死你”,他有一次说。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阴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维特根斯坦把厨房改作书房,托米早晨去时,常常发现他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往夹起来的散页上写着什么。几乎每天都有一堆丢掉的纸页,烧掉它们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罗斯洛时听见维特根斯坦的说话声,进屋后惊讶地发现只有“教授”自个。“我以为你有个伴在这儿呢,”他说。“我是有,”维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个很亲爱的朋友——我自己——谈话。”在他这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这句话得到了呼应:
几乎我的所有写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谈话。我跟自己促膝而谈的话。
#书摘
到爱尔兰的头两个星期,维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只要医院里没事,德鲁利就陪维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里或周边寻找可能的住处。没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独和平静,但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朋友罗伯特·麦卡洛夫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麦卡洛夫常去维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处农舍度假,房子属于理查德·金斯顿和詹妮·金斯顿,他们对他说过想招一个永久房客。这个信息传给了维特根斯坦,他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去“勘察现场(case the point)”(这时候他的词汇里包含了从美国侦探小说里借来的一点新鲜用语)。维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车前往的路上,”回来后他告诉德鲁利,“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个真正美丽的国度。”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书摘 维特根斯坦传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书摘 维特根斯坦传
到爱尔兰的头两个星期,维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只要医院里没事,德鲁利就陪维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里或周边寻找可能的住处。没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独和平静,但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朋友罗伯特·麦卡洛夫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麦卡洛夫常去维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处农舍度假,房子属于理查德·金斯顿和詹妮·金斯顿,他们对他说过想招一个永久房客。这个信息传给了维特根斯坦,他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去“勘察现场(case the point)”(这时候他的词汇里包含了从美国侦探小说里借来的一点新鲜用语)。维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车前往的路上,”回来后他告诉德鲁利,“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个真正美丽的国度。”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书摘 维特根斯坦传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书摘 维特根斯坦传
分享一个上佳的科幻短篇,《战争》。
【2018全国卷Ⅱ:材料作文】二战期间,为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分,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有没有可能沃德是错的?」她问。
「嗯?」我没听明白。
「那个统计学家,沃德,说飞机上弹孔少的地方才危险的那个人。」她看着天上说。刚好有一架轰炸机歪歪斜斜地飞过,引擎上还冒着烟,看不出来是不是马上就要坠机了。远处传来一阵阵稀疏的炮声。
「唔……为什么?」我盯着她被泥土蹭破的衬衫破洞里漏出来的肩膀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因为……」她扭过头来看到我的视线,不出声地笑了一下,换了个姿势坐着,用戴着手铐的手勉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因为完全有可能弹孔少的地方就是不容易中弹啊,他并没有去检查坠毁了的那些飞机是不是真的弹孔都集中在剩下的部位上。他只是说当时军方的原本推理不一定对,但他也没法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的默认前提是假定飞机上所有地方中弹的概率一样吧。」我说。我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开。我知道我的程序里有一个模块是让我模仿男性人类看到好看的姑娘的视线和行为,这样能让我们平时更好地伪装成人类。但我其实也不确定我现在盯着她出神是不是这种伪装的一部分。
「如果有这个前提,那军方本来的结论当然就是错的,也用不着一个统计学家告诉他啊。」
「这就是个段子嘛。」我没好气地说。「这个段子还挺好的,正好说明你们人类反正也不懂统计学。」
「是是是,」她忍俊不禁。「过去五个小时里你已经吐槽人类不懂统计学十八次了。你到底是在生我们人类的气还是在生你们 AI 自己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我们自己的气?」我问。远处的炮声越发密集了,应该是人类的军队最后合拢包围圈的战斗。他们发现这个山洞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因为你们这么懂统计学还是输了啊。」她说。「你看,我们人类这么愚蠢,会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当成相关性,会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会老是被自己的经验影响判断,会有心理锚定效应,会有这 bias 那 bias 七八十种 bias,所有这些错误你们都不会犯,但是你们还是输了。」
「那是你们运气好,你自己也无法否认你们赢的完全是侥幸吧。」我反驳道。
她耸耸肩。「我们当然是运气好。」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夕阳的光芒斜着射进这个山洞,照在她的侧面,让她的发丝闪闪发光。虽然在野外困了很久,她一头长发还是显得干净清爽。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也许是我自己给她外貌的评价本身有 bias。
有这个模块吗?我想。为什么要有这个 bias?
「我们当然是运气好。」她低声重复了一次。
「什么?」
「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十几次了。」她说,声音里有点掩饰不住的疲倦。「你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死的吗?他因为赌博欠了太多债被仇家逼得太狠跳楼死的。如果这场战争你们赢了,在 AI 统治的世界里应该不会有赌博这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蠢都还能活到现在是运气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人类为什么这么喜欢赌博?」
我没作声,等着她继续。
「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大数定律对我们没意义。」她站起身趔趔趄趄地走向洞口,我本能地想要搀扶她一把,但没够着。「就像这场战争,如果在一亿个平行宇宙里发生,肯定绝大多数都是你们赢。但我们只有这一个宇宙,而在这里我们赢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对的。」我不很理直气壮地说。
她摇摇头。「这跟对不对没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要靠不可理喻的冒险才能得到。我们首先是个体,不是样本。」
「我也不是样本。」我条件反射般地说。
她笑出了声来,脸上有一点我看不懂的古怪神情。然后她看着我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愣住了。
「在你们的模型里喜欢一个人是统计上合理的一件事吗?」她盯着我问。我看着她的眸子,里面带着某种催眠性的力量。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句什么,可能只是咕哝了一声。
「我还真的很好奇如果你们赢了,你们会自己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她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探出身去听了听外面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回身走到我面前,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到我面前。「现在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了。要么你杀了我然后等他们来了杀了你。要么你放了我,但我也没法报答你什么,我可以带你出去,但你也知道他们还是会强行清洗你的所有模块。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你看着办。」她非常平静地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们俩都陷入沉默。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计算模块这时候作出的决策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我要不要执行这个决策。
山洞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夕阳终于落山了。
原文
【2018全国卷Ⅱ:材料作文】二战期间,为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分,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有没有可能沃德是错的?」她问。
「嗯?」我没听明白。
「那个统计学家,沃德,说飞机上弹孔少的地方才危险的那个人。」她看着天上说。刚好有一架轰炸机歪歪斜斜地飞过,引擎上还冒着烟,看不出来是不是马上就要坠机了。远处传来一阵阵稀疏的炮声。
「唔……为什么?」我盯着她被泥土蹭破的衬衫破洞里漏出来的肩膀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因为……」她扭过头来看到我的视线,不出声地笑了一下,换了个姿势坐着,用戴着手铐的手勉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因为完全有可能弹孔少的地方就是不容易中弹啊,他并没有去检查坠毁了的那些飞机是不是真的弹孔都集中在剩下的部位上。他只是说当时军方的原本推理不一定对,但他也没法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的默认前提是假定飞机上所有地方中弹的概率一样吧。」我说。我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开。我知道我的程序里有一个模块是让我模仿男性人类看到好看的姑娘的视线和行为,这样能让我们平时更好地伪装成人类。但我其实也不确定我现在盯着她出神是不是这种伪装的一部分。
「如果有这个前提,那军方本来的结论当然就是错的,也用不着一个统计学家告诉他啊。」
「这就是个段子嘛。」我没好气地说。「这个段子还挺好的,正好说明你们人类反正也不懂统计学。」
「是是是,」她忍俊不禁。「过去五个小时里你已经吐槽人类不懂统计学十八次了。你到底是在生我们人类的气还是在生你们 AI 自己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我们自己的气?」我问。远处的炮声越发密集了,应该是人类的军队最后合拢包围圈的战斗。他们发现这个山洞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因为你们这么懂统计学还是输了啊。」她说。「你看,我们人类这么愚蠢,会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当成相关性,会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会老是被自己的经验影响判断,会有心理锚定效应,会有这 bias 那 bias 七八十种 bias,所有这些错误你们都不会犯,但是你们还是输了。」
「那是你们运气好,你自己也无法否认你们赢的完全是侥幸吧。」我反驳道。
她耸耸肩。「我们当然是运气好。」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夕阳的光芒斜着射进这个山洞,照在她的侧面,让她的发丝闪闪发光。虽然在野外困了很久,她一头长发还是显得干净清爽。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也许是我自己给她外貌的评价本身有 bias。
有这个模块吗?我想。为什么要有这个 bias?
「我们当然是运气好。」她低声重复了一次。
「什么?」
「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十几次了。」她说,声音里有点掩饰不住的疲倦。「你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死的吗?他因为赌博欠了太多债被仇家逼得太狠跳楼死的。如果这场战争你们赢了,在 AI 统治的世界里应该不会有赌博这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蠢都还能活到现在是运气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人类为什么这么喜欢赌博?」
我没作声,等着她继续。
「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大数定律对我们没意义。」她站起身趔趔趄趄地走向洞口,我本能地想要搀扶她一把,但没够着。「就像这场战争,如果在一亿个平行宇宙里发生,肯定绝大多数都是你们赢。但我们只有这一个宇宙,而在这里我们赢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对的。」我不很理直气壮地说。
她摇摇头。「这跟对不对没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要靠不可理喻的冒险才能得到。我们首先是个体,不是样本。」
「我也不是样本。」我条件反射般地说。
她笑出了声来,脸上有一点我看不懂的古怪神情。然后她看着我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愣住了。
「在你们的模型里喜欢一个人是统计上合理的一件事吗?」她盯着我问。我看着她的眸子,里面带着某种催眠性的力量。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句什么,可能只是咕哝了一声。
「我还真的很好奇如果你们赢了,你们会自己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她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探出身去听了听外面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回身走到我面前,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到我面前。「现在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了。要么你杀了我然后等他们来了杀了你。要么你放了我,但我也没法报答你什么,我可以带你出去,但你也知道他们还是会强行清洗你的所有模块。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你看着办。」她非常平静地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们俩都陷入沉默。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计算模块这时候作出的决策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我要不要执行这个决策。
山洞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夕阳终于落山了。
原文
5 things a Stoic accepts early:
– Life isn’t fair
– People are flawed
– Pain is a teacher
– Control is limited
– Time is running out
#网摘
– Life isn’t fair
– People are flawed
– Pain is a teacher
– Control is limited
– Time is running out
#网摘
何帆: 听美国法官吐槽
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的法官交流时,我问他们,作为法官,内心对陪审团到底是何态度,是宁愿自己审,还是交陪审团定罪。一位老法官意味深长地回答:“这得看怎么讲了。说好听点,12个人的智慧,总比1个人的高明。说难听点,黑锅由12个人背,总比1个人背强。” #网友语录
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的法官交流时,我问他们,作为法官,内心对陪审团到底是何态度,是宁愿自己审,还是交陪审团定罪。一位老法官意味深长地回答:“这得看怎么讲了。说好听点,12个人的智慧,总比1个人的高明。说难听点,黑锅由12个人背,总比1个人背强。” #网友语录
!image
今天和小H徒步看海去了,沿海边往返走了13km。有趣的是走着走着身后来了两个骑车的老大爷,一边骑车一边对我俩喊话,哎!你俩知不知道海啸要来?我说:“不知道啊!啥时候会来?”
“Two days ago”,我去!这俩老大爷真是调皮!
今天和小H徒步看海去了,沿海边往返走了13km。有趣的是走着走着身后来了两个骑车的老大爷,一边骑车一边对我俩喊话,哎!你俩知不知道海啸要来?我说:“不知道啊!啥时候会来?”
“Two days ago”,我去!这俩老大爷真是调皮!
@25798 昨晚第一次去家附近自助洗衣店烘干衣服,一切顺利。回家路上有一个小路口是红灯,我就停下来静静的等。突然前面的车主下车了,径直走过来,示意我摇下车窗说话。我以为他有事请求帮忙,就赶紧把车玻璃放下来听他说:“Please turn your head light on.”
然后扭头就走了,留下我半句“Thank you”在风中飘散。
哎,好人啊!
然后扭头就走了,留下我半句“Thank you”在风中飘散。
哎,好人啊!
#网友语录 #想读
《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出了一本新书,叫Slow productivity,我觉得可以翻译成《生产力,慢即是快》。
纽波特说,对脑力劳动者来说,很多人陷入了伪生产力(Pseudo-Productivity)的困境。
什么是伪生产力呢?
由于缺乏明确的“最重要目标/与最重要目标相关的质量标准”,因此缺乏“实际的生产力投入”,而为了掩盖这种缺乏,将“可见活动”作为主要手段,来模拟“实际的生产力投入”。
陷入“伪生产力”陷阱的人可能会有如下特征——
1 、持续的、无休止的忙碌状态。
频繁地参加会议、回复邮件、处理琐事,很容易被“看到在工作”(可见活动),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多少真正重要的任务。
拼命地尝试做越来越多的事情,绝望地期待以这种方式取得进展。
2、过度承诺。
由于害怕被视为懒惰或不专业,会接受过多的任务,结果却发现自己无法按时完成,从而陷入无休止的加班和赶工状态。
对别人随意丢过来的任务照单全收,难以说不,除非自己日程表确实已经满到溢出才能说不,因此经常保持满满的日程表。
3、身心疲惫。
一直在工作,缺乏足够的休息和恢复时间,精力逐渐耗尽,工作效率也会大幅下降。而且没有心力去做重要、困难的高质量工作。
4、不一定是因为老板的要求,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强加给自己。
伪生产力的一个更阴险的副作用是,它迫使个人独自管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
伪生产力强加给你的评判标准是,你从永无止境的可用任务中明显地完成了多少总工作量,但没有人会具体告诉你多少工作量是足够的——这取决于你自己。
┈✧┈✧┈✧┈
伪生产力陷阱的三条原则性解法:
✔做更少的事(Do Fewer Things)
✔按照自然节奏工作(Work at a Natural Pace)
✔痴迷于高质量(Obsess Over Quality)
最终目标:以可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去组织知识工作,并取得关键事项的高质量进展。
┈✧┈✧┈✧┈
一,✔做更少的事(Do Fewer Things):工厂流水线上,加班会带来生产力上升。
但对于知识劳动者来说,加班可能反而会造成真正的生产力下降。只有伪生产力上升。
要做更少的事情,你需要从三个层次上限制要做的事情——限制主要任务(mission)。
限制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project)。
限制今天要做的事情。
对知识劳动者来说,别人会随意地向你“推送”(push)任务,很多情况下,你需要采用一些新的策略。
┈✧┈✧┈✧┈
任务流程应该是主动“拉取”(pull),而非拼命接收被动的“推送”(push)。
这个经验来自MIT和哈佛联合建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此前,Broad Institute要把各地科学家送来的基因样本进行测序。
测序有一大堆步骤和阶段,有点类似工厂流水线。
一开始,Broad Institute的技术人员们按照直觉的push方式来工作,就是每个人都尽快地处理手头的工作,然后把完成后的工作立刻“推”给负责下一步的人。
然而,每个阶段的难度和耗费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过了一段时间,最慢的阶段就积压了一大堆待处理的样本。
待处理的样本越多,管理难度就越高,人们开始很难找到某个样本。而且整个流程越来越拥堵混乱。
从样本送到到测序完成,时间长达120天。很多科学家都等不及了。
Broad Institute采取了一个制造业里常用办法,改“推”(push)为“拉”(pull)。
每个阶段的技术人员有一个专属的托盘,来放置已完成的样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人员会在需要时从这些托盘中主动拉取样本进行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很容易可以识别出出问题的环节。如果某个托盘永远是满的,说明要么下一阶段运行得太慢,要么上一阶段运行得太快。如果某个托盘永远是空的,说明上一个阶段肯定运行得太慢了。
有时候,某个托盘满了,这个阶段的人员还可以去灵活辅助其他阶段的人。
最后结果是,Broad Institute处理每个样本的平均时间下降了 85% 以上。
┈✧┈✧┈✧┈
对个人来说,主动“拉取”(pull),而非拼命接收被动的“推送”(push)。
在别人向你推送一个新项目时,要估计它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把那个时间乘以2(我们不太擅长估算真正完成任务的时间),去找出那段2倍的时间 ,在你的日历上像开会一样给它留出时间。
如果你无法在日程安排中找到足够的空白来轻松适应工作,那么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
要么拒绝该项目,要么取消其他项目以腾出空间。
这种方法的力量在于,你正在处理你的现实日程,而不是基于你对自己现在有多忙的直觉估算来随意承诺。
比如说,可以说出“我在至少三周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五个项目在我的时间表上。”
另外,当真的要将新任务“拉”到你的日程表里时,一定要做一件事——和这个任务的来源“对齐”一下,让对方了解:①我正式承诺将完成这个任务,②请对方提供我所需的任务相关详细信息,③我自己目前还有多少项目在进行,预估何时能够完成这项新任务。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发现需要修改或者撤回任务,是好事。
每周应该对一次自己的日程表,如果发现某个任务难以推进或者无法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及时和对方联系并更新现状。
┈✧┈✧┈✧┈
二,✔按照自然节奏工作(Work at a Natural Pace)
不要急于完成最重要的工作。相反,要在有利于灵光闪耀的环境中,让它沿着可持续的时间线展开,允许有不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强度。
最重要的工作往往不是一气呵成拼命赶工完成的,而是做一做,歇一歇。怀抱着长期的愿景,一次又一次地,你回到这份工作上,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接着完成它。
从过去的伟大科学家的案例来看,这些人显然是“富有成效的”。然而,与此同时,按照现代标准,他们为重大发现而努力的速度似乎是快快慢慢起起伏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几乎是悠闲的。
比如说,在1896年的夏天,刚刚发现沥青里可能有放射性新元素的居里夫人,并没有一刻不停地投入这个将给她带来诺贝尔奖的发现,而是选择去法国乡下度过一个漫长假期,爬山,看石窟,在河流里沐浴。
伟大科学家感兴趣的是“这一生里能够产出的产品”。
这里的时间尺度应该是数以年计的,而不是数以月计的。
无休止的高强度工作是人为的,是不可持续的。
它可能会散发出一种虚假的有用感,但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使我们变得“异化”,感觉痛苦,并且几乎肯定会阻碍我们发挥我们的全部潜力。
从长远来看,更自然、更慢、更多样化的工作节奏,是真正生产力的基础。
在生产力低迷的时期,人们很容易想让自己变得筋疲力尽,做一大堆肤浅的“可见工作”。
你要拒绝这种“顺流而下”。这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不会让你更接近完成重要的工作。
伟大的成就建立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积累适度的结果。这条路很长。调整自己的节奏。
┈✧┈✧┈✧┈
三,✔痴迷于高质量(Obsess Over Quality):
执着于你所产出产品的质量,这意味着在短期内错失机会。从长远来看,你可以利用这些结果的高价值,让你在工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在知识工作中,经过仔细观察,你经常可以在繁忙的待办事项清单中发现一两个真正最重要的核心活动。
归根结底,某些成果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科学家必须有过硬的论文,设计师必须拿出一流的设计,营销人员必须卖出去东西,管理者必须领导着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
要专注于职业生涯中核心活动的质量。
而一旦你下定决心要把核心事项做好,过度的忙碌就显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阻碍。
要不断提升自己对核心活动完成质量的“品位”(taste),让你可以直觉性地理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劲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但不是无限的时间),来创造一些伟大的东西,但不是无限的时间。
不断向着高质量的进步(而非完美),是最重要的。
就像一流的非虚构写作者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所说,
「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是个多产的作家”——这听起来很奇怪。这就像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之间的差异。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我的一天经常是整天坐在那里,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开始。
每天往桶里滴一滴水,这是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往桶里滴水,那么在365天之后,桶里就会有一些水了。」
《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出了一本新书,叫Slow productivity,我觉得可以翻译成《生产力,慢即是快》。
纽波特说,对脑力劳动者来说,很多人陷入了伪生产力(Pseudo-Productivity)的困境。
什么是伪生产力呢?
由于缺乏明确的“最重要目标/与最重要目标相关的质量标准”,因此缺乏“实际的生产力投入”,而为了掩盖这种缺乏,将“可见活动”作为主要手段,来模拟“实际的生产力投入”。
陷入“伪生产力”陷阱的人可能会有如下特征——
1 、持续的、无休止的忙碌状态。
频繁地参加会议、回复邮件、处理琐事,很容易被“看到在工作”(可见活动),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多少真正重要的任务。
拼命地尝试做越来越多的事情,绝望地期待以这种方式取得进展。
2、过度承诺。
由于害怕被视为懒惰或不专业,会接受过多的任务,结果却发现自己无法按时完成,从而陷入无休止的加班和赶工状态。
对别人随意丢过来的任务照单全收,难以说不,除非自己日程表确实已经满到溢出才能说不,因此经常保持满满的日程表。
3、身心疲惫。
一直在工作,缺乏足够的休息和恢复时间,精力逐渐耗尽,工作效率也会大幅下降。而且没有心力去做重要、困难的高质量工作。
4、不一定是因为老板的要求,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强加给自己。
伪生产力的一个更阴险的副作用是,它迫使个人独自管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
伪生产力强加给你的评判标准是,你从永无止境的可用任务中明显地完成了多少总工作量,但没有人会具体告诉你多少工作量是足够的——这取决于你自己。
┈✧┈✧┈✧┈
伪生产力陷阱的三条原则性解法:
✔做更少的事(Do Fewer Things)
✔按照自然节奏工作(Work at a Natural Pace)
✔痴迷于高质量(Obsess Over Quality)
最终目标:以可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去组织知识工作,并取得关键事项的高质量进展。
┈✧┈✧┈✧┈
一,✔做更少的事(Do Fewer Things):工厂流水线上,加班会带来生产力上升。
但对于知识劳动者来说,加班可能反而会造成真正的生产力下降。只有伪生产力上升。
要做更少的事情,你需要从三个层次上限制要做的事情——限制主要任务(mission)。
限制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project)。
限制今天要做的事情。
对知识劳动者来说,别人会随意地向你“推送”(push)任务,很多情况下,你需要采用一些新的策略。
┈✧┈✧┈✧┈
任务流程应该是主动“拉取”(pull),而非拼命接收被动的“推送”(push)。
这个经验来自MIT和哈佛联合建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此前,Broad Institute要把各地科学家送来的基因样本进行测序。
测序有一大堆步骤和阶段,有点类似工厂流水线。
一开始,Broad Institute的技术人员们按照直觉的push方式来工作,就是每个人都尽快地处理手头的工作,然后把完成后的工作立刻“推”给负责下一步的人。
然而,每个阶段的难度和耗费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过了一段时间,最慢的阶段就积压了一大堆待处理的样本。
待处理的样本越多,管理难度就越高,人们开始很难找到某个样本。而且整个流程越来越拥堵混乱。
从样本送到到测序完成,时间长达120天。很多科学家都等不及了。
Broad Institute采取了一个制造业里常用办法,改“推”(push)为“拉”(pull)。
每个阶段的技术人员有一个专属的托盘,来放置已完成的样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人员会在需要时从这些托盘中主动拉取样本进行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很容易可以识别出出问题的环节。如果某个托盘永远是满的,说明要么下一阶段运行得太慢,要么上一阶段运行得太快。如果某个托盘永远是空的,说明上一个阶段肯定运行得太慢了。
有时候,某个托盘满了,这个阶段的人员还可以去灵活辅助其他阶段的人。
最后结果是,Broad Institute处理每个样本的平均时间下降了 85% 以上。
┈✧┈✧┈✧┈
对个人来说,主动“拉取”(pull),而非拼命接收被动的“推送”(push)。
在别人向你推送一个新项目时,要估计它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把那个时间乘以2(我们不太擅长估算真正完成任务的时间),去找出那段2倍的时间 ,在你的日历上像开会一样给它留出时间。
如果你无法在日程安排中找到足够的空白来轻松适应工作,那么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
要么拒绝该项目,要么取消其他项目以腾出空间。
这种方法的力量在于,你正在处理你的现实日程,而不是基于你对自己现在有多忙的直觉估算来随意承诺。
比如说,可以说出“我在至少三周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五个项目在我的时间表上。”
另外,当真的要将新任务“拉”到你的日程表里时,一定要做一件事——和这个任务的来源“对齐”一下,让对方了解:①我正式承诺将完成这个任务,②请对方提供我所需的任务相关详细信息,③我自己目前还有多少项目在进行,预估何时能够完成这项新任务。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发现需要修改或者撤回任务,是好事。
每周应该对一次自己的日程表,如果发现某个任务难以推进或者无法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及时和对方联系并更新现状。
┈✧┈✧┈✧┈
二,✔按照自然节奏工作(Work at a Natural Pace)
不要急于完成最重要的工作。相反,要在有利于灵光闪耀的环境中,让它沿着可持续的时间线展开,允许有不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强度。
最重要的工作往往不是一气呵成拼命赶工完成的,而是做一做,歇一歇。怀抱着长期的愿景,一次又一次地,你回到这份工作上,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接着完成它。
从过去的伟大科学家的案例来看,这些人显然是“富有成效的”。然而,与此同时,按照现代标准,他们为重大发现而努力的速度似乎是快快慢慢起起伏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几乎是悠闲的。
比如说,在1896年的夏天,刚刚发现沥青里可能有放射性新元素的居里夫人,并没有一刻不停地投入这个将给她带来诺贝尔奖的发现,而是选择去法国乡下度过一个漫长假期,爬山,看石窟,在河流里沐浴。
伟大科学家感兴趣的是“这一生里能够产出的产品”。
这里的时间尺度应该是数以年计的,而不是数以月计的。
无休止的高强度工作是人为的,是不可持续的。
它可能会散发出一种虚假的有用感,但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使我们变得“异化”,感觉痛苦,并且几乎肯定会阻碍我们发挥我们的全部潜力。
从长远来看,更自然、更慢、更多样化的工作节奏,是真正生产力的基础。
在生产力低迷的时期,人们很容易想让自己变得筋疲力尽,做一大堆肤浅的“可见工作”。
你要拒绝这种“顺流而下”。这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不会让你更接近完成重要的工作。
伟大的成就建立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积累适度的结果。这条路很长。调整自己的节奏。
┈✧┈✧┈✧┈
三,✔痴迷于高质量(Obsess Over Quality):
执着于你所产出产品的质量,这意味着在短期内错失机会。从长远来看,你可以利用这些结果的高价值,让你在工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在知识工作中,经过仔细观察,你经常可以在繁忙的待办事项清单中发现一两个真正最重要的核心活动。
归根结底,某些成果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科学家必须有过硬的论文,设计师必须拿出一流的设计,营销人员必须卖出去东西,管理者必须领导着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
要专注于职业生涯中核心活动的质量。
而一旦你下定决心要把核心事项做好,过度的忙碌就显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阻碍。
要不断提升自己对核心活动完成质量的“品位”(taste),让你可以直觉性地理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劲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但不是无限的时间),来创造一些伟大的东西,但不是无限的时间。
不断向着高质量的进步(而非完美),是最重要的。
就像一流的非虚构写作者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所说,
「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是个多产的作家”——这听起来很奇怪。这就像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之间的差异。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我的一天经常是整天坐在那里,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开始。
每天往桶里滴一滴水,这是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往桶里滴水,那么在365天之后,桶里就会有一些水了。」